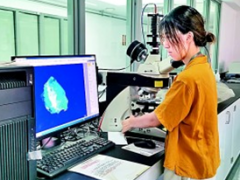切尔诺贝利发生核事故的5分钟后,凌晨1点28分,第一批消防员赶到了现场。
抬头望去,4号机组的厂房已经被炸掉一半,烈火正在吞噬剩余的墙体。
消防员看不见那些致命的“杀手”——爆炸释放出的大量放射性物质(主要是铯-137和锶-90),他们只想扑灭眼前的大火。
为了避免大火烧到其他反应堆,由普拉维克中尉率领的消防队立刻采取行动。
他们身穿平时用的消防服和头盔,攀登上厂房的屋顶,试图靠近着火点。
没过多久,身经百战的消防员们出现了从未有过的状况,恶心呕吐,难以站立,感觉“像是病了”。
核电站的值班医生赶来询问,是否有人烧伤。
消防员的回答却令人更加不安:“没有,情况还不明确,某些东西让我的小伙子们不太舒服。”
到早晨7点,参与救火的消防员全部被送往医院,其中很多人出现皮肤发红、溃疡、出血、呕吐等症状,包括普拉维克在内,有28人在随后三个月内死于急性放射病。
灾难降临的这一天,是1986年4月26日,位于乌克兰首都基辅以北130公里的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了史上最严重的核事故之一。
据联合国专题报道,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发生后,估计有840万人受到辐射影响、15.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受到污染、60万人参与救援和清理行动、40万人被迫离开故土。
伴随着这一串触目惊心的数字,恐惧蔓延到世界各地,时至今日,当年受灾最严重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俄罗斯的部分地区,仍然处于核灾的阴影之中。
切尔诺贝利事件发生时,冷战正逐渐进入尾声,欧洲各国并未及时得到来自苏联的消息。
第二天,在距离切尔诺贝利1000多公里的瑞典福斯马克核电厂,有工人检测发现其衣服上沾有放射性物质(超过正常值100倍),而这些辐射物并不是来自本地的核电厂。
20世纪,核动力登上历史舞台,开启了原子能时代。
在安全的情况下,核能无疑是一种清洁、高效的能源,但也存在诸多风险。因此,世界各地的“反核运动”此起彼伏,比如1979年美国三里岛核电站事故发生后,有20万人举行了反对使用核电站的示威。
现在,福斯马克核电厂检测到欧洲放射性水平发生的变化,这引起了瑞典人的高度警惕。
专家们结合风向制作出一张地图,根据辐射物的来源,推测苏联某地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核事故。瑞典政府与苏联取得联系,但没有收到苏联当局的肯定答复。
此时,苏联的很多民众甚至官员也不知道切尔诺贝利发生了什么。
核事故的发生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位于乌克兰北部的旷野,自1977年投入使用,共有4台机组,此次发生爆炸的是第4机组的核反应堆。
为了安置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建筑工人及工作人员,苏联政府曾在靠近乌克兰和白俄罗斯边境的地方兴建了一座城镇——普里皮亚季。
这座小镇多次被评为“模范市镇”,核事故发生前,普里皮亚季有居民50000人,他们很多人在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工作,代表着苏联核工业的未来,也将这座小镇当成了一生的归宿。这里的游乐园、游泳池、体育馆、医院、酒店都曾留下他们的足迹。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站长布里奇哈诺夫,曾经在报纸上发表了一番骄傲的言论:
“1977年将被载入苏联核工业发展史,这一年在普里皮亚季诞生了一位核能巨子。”
然而,核事故发生时,距离切尔诺贝利第一座核反应堆开始工作,仅仅过去了9年。
1986年4月26日,在一声恐怖的巨响之后,切尔诺贝利第4号机组赤焰如柱,黑烟遮天,水泥块、玻璃碴、石墨渣、燃料棒碎片落满一地,犹如一幅末世景象。
事故当晚的消防员,成为第一批牺牲者。
他们曾经无数次地扑灭火焰,却对辐射无能为力,救火时接触的放射物开始摧毁他们的身体。在高辐射的直接影响下,医生也无法拯救这些病人。
普拉维克中尉是最先赶到现场的消防员之一。
他在当地有一个美好的家庭。热爱读书写字的他保留了给妻子写信的习惯,总喜欢用书信来表达对妻子的爱意,有时他会在清晨陪父母亲干农活。
但这一天,普拉维克的家人迟迟等不到他回家。当听到普拉维克被送到普里皮亚季的医院时,他们才急忙冲去医院看望他。
普拉维克此时已经得知事态的严重性,于是他隔着窗户,告诉家人,让妻儿现在就带上行李,骑摩托车前往位于乌克兰中部的岳父岳母家避难。家人们照着普拉维克的指示行动,出门前,妻子在家中留下了一封书信。
这是一封注定没有回信的情书。
4月28日,苏联政府终于在电视上公开承认切尔诺贝利发生核事故,但并没有说明核辐射的严重程度,此时,撤离及清理行动正在争分夺秒地进行中。
在晚间新闻中,一名播音员用寥寥数语念出了电视台早已拟好的新闻稿,也没有提及辐射值上升以及当地居民撤离的消息:
切尔诺贝利原子能电站发生了事故,一座原子能反应堆受损,政府正采取措施消除事故带来的影响,给予受害者援助。相关政府委员会已成立,以查明事故起因。
切尔诺贝利事件让本就不乐观的苏联局势雪上加霜,尤其是受核辐射影响最严重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等地区,随着核事故的流言四起,爆发了抗议运动。
这也难怪,苏联最后一位领导人戈尔巴乔夫将切尔诺贝利当作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说:“比起我发起的开放改革举措,可能切尔诺贝利事件才是苏联解体的真正原因。”
切尔诺贝利事件之后,戈尔巴乔夫成为了一名忠实的环保主义者,后来多次把切尔诺贝利写进他的畅销书中。
时间拨回到1986年4月26日的1点23分。
这是切尔诺贝利4号核反应堆发生爆炸的时间。
国际原子能机构将切尔诺贝利核事故定为最高第七级事件,做过多次调查,但关于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起因,有两份观点迥异的官方报告。
第一份报告(INSAG-1)认为,切尔诺贝利核事故是一起由于操作失误引发的“人祸”。
事发当晚,厂长布里奇哈诺夫并不在场,控制室内负责操作反应堆的主要人员是:时年55岁的副总工程师迪亚特洛夫;拥有10年电站工作经验的第9操作组值班主任阿西莫夫;年轻的新手操作员托普图诺夫。
本来是看似稳如老狗的老中青三代组合,却闹出了前所未有的大动静。
报告显示:“在后备涡轮测试的准备与执行阶段,操作人员关闭了一系列保护系统,违反了技术操作最重要的安全规定。”当时,为了重现测试所需的紧急情况,操作员关闭了紧急核心冷却等几个系统,随后又为了尽快完成测试而随意操作。
后来,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调查委员会主任委员、苏联专家勒加索夫对此批评道:“这就好比飞行员一边飞行,一边测试飞机的引擎。”
按预定计划,当天凌晨1点23分,4号核反应堆将关闭其中一个反应器20秒,并进行发电机能力测试。
但因违规操作,4号核反应堆的功率在短时间内激增至最大设计负荷的约10倍,7秒后导致灾难性的蒸汽爆炸,造成火灾。
反应炉的设计者认定不可能发生这种“关闭安全系统又肆意操作”的情况,所以并未设计一个强制系统阻止事故发生。
另外,切尔诺贝利核电站采用的RBMK反应堆属于早期的核电系统,只设计了单一的防护层,不像后来的核电站在反应堆外还建有安全壳,爆炸后墙体垮塌,核反应堆炉心暴露在外,迅速向大气释放了520种危险的放射性核素,同一核电厂的1、2、3号机组被迫停止运转。
灾难由此爆发。
而在另一份报告(INSAG-7)中,则说发生爆炸的主要原因并不是操作人员的失误,而是反应炉的设计本身存在缺陷,容易造成“正空泡效应”等反应,导致安全隐患。
如此一来,切尔诺贝利核事故的起因陷入了罗生门。
不难看出来,这是苏联政府、乌克兰政府、国际原子能机构与反应炉设计者等各方势力的“极限拉扯”。
事已至此,如何化解此次危机,成为苏联要面对的难题。
爆炸发生后,在现场附近测出了致命量数百倍的核辐射,距离30公里内的居民需要紧急撤离。
4月27日中午,即公开核事故消息前,苏联政府用于疏散居民的1000多辆客车及3列火车便已到达,随后将普里皮亚季与切尔诺贝利的53000名居民与员工全部撤出,并在200公里外的斯拉武特奇安置疏散的居民。
普里皮亚季播送了一条紧急疏散广播,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他们已经永远回不了家园。
事故后36小时,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周围的全部居民撤离完毕。有专家判断,普里皮亚季及附近地区在此后的几个世纪内将不再适合人类居住。有数据统计,各地因切尔诺贝利核事故而背井离乡的居民多达40万人。
切尔诺贝利4号核反应堆内部的火灾持续了10天,除了反应堆中剩余的800吨石墨引起的大火,还有约50吨核燃料在爆炸瞬间化作烟尘进入大气层,另有70吨核燃料和900吨石墨分散在反应堆周围。
之后一周,直升机不断飞向核电站上空,先后从空中向反应堆炉芯倾倒了5000吨的硼砂,才停止了反应堆中的链式反应。
但,直升机投掷的5000吨材料,让本就遭受重创的建筑物更加摇摇欲坠。同时,4号机组内近千吨温度高达1200°C的石墨块与堆芯熔融物不断向下融穿几层混凝土楼层后,可能会遇到地下室内积存的高放射性废水,导致水蒸汽爆炸,完全摧毁4号反应堆,甚至使放射物飘散到欧洲各地。
5月2日,切尔诺贝2号反应堆的技术人员、高级机械工程师阿纳年科,第2涡轮车间控制单元高级工程师别兹帕洛夫和切尔诺贝利反应堆值班长巴拉诺夫三人,接受了一个危险系数极高的任务——身着防护服,潜水进入4号反应堆被淹没的地下室,打开排水闸门,避免又一次爆炸的发生。
其中,阿纳年科由于平时的工作而熟知闸门所在位置,别兹帕洛夫清楚地了解阀门如何控制,巴拉诺夫则负责照明。
很多人认为,这次行动必死无疑,甚至三人可能在到达排水阀前就会被高辐射杀死。
然而,阿纳年科等人凭借着对地下室路径熟悉,避开了高辐射积水区域,之后找到排水阀并打开,抽取了地下室内的废水。
数个月后,炉芯的放射性熔融物果然和当初的预计一样,烧穿了楼板,但由于地下室内的放射性冷却水早已排空,并没有发生蒸气爆炸。
更幸运的是,三位冒着生命危险下水关闭阀门的英雄,安全地完成任务,回到地面。
根据阿纳年科的口述,他们在事先计划好一切后,以最快的时间下潜到地下室,到达指定位置,随后在阴暗狭窄的水下迅速找到了一个阀门。
阿纳年科还记得,当时打开阀门的兴奋情绪:“过了几分钟后,我们听到了水流特有的噪声,并且感觉到水位在下降——水终于往外排了!”
人类的赞歌,就是勇气的赞歌。在核灾难面前,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肉体,去力挽狂澜。
5月4日后,石油钻机钻入反应堆地下,每天向里面注入25吨液氮,使反应堆地下土壤冻结在零下100摄氏度左右,避免反应堆炉芯熔融物不断下降污染地下水。直到专家评估4号反应堆的核裂变已经不会融穿,才在隧道内灌满混凝土后封闭。
此后几个月,苏联政府派出24万军人、工人,在炸毁的4号反应堆外部修建了钢筋混凝土的“石棺”,将事故现场彻底封闭起来,以免辐射持续扩散。
“石棺”只是一种临时防御措施,仅有30年左右的使用寿命。由于现场辐射量过高,很多地方在施工时缺乏必要的焊接,甚至连螺丝钉也没有。
一旦“石棺”发生倒塌,反应堆内大量的放射性尘埃将再度扩散到空气中。
因此,苏联解体后,由欧美各国建立的切尔诺贝尔基金,提出“遮蔽执行计划”,在4号机组外围建造一个新的遮蔽结构体,即“新石棺”。
该工程已于2019年完工,就国际合作的规模而言,它是核安全领域有史以来最大的项目之一。
历时三十多年,切尔诺贝利事件的后续工作仍在进行。这需要各个国家的携手努力以及漫长的等待。
切尔诺贝利核电站的故事,并没有在这次事故后画下句号。
除了发生爆炸的第4号机组外,其余三台机组仍照常运行了十几年时间,直到2000年才彻底关闭,结束了输送电力的使命。
事故发生后几年内,陆续有人返回切尔诺贝利工作。
截至2016年,普里皮亚季的“无人区”住着140名居民。81岁的老人伊万是核事故后重返家园的核电站工人,他和妻子玛丽亚一直生活在这里。
有记者采访了生活在隔离区的伊万,他说:“你问我们回家后的生活怎样?我回来后,就跑到切尔诺贝利核电站打工。生活已经改变了,很多事情都变了。”
“过去,这里有人居住。突然间,他们都不见了。过去这里充满了生活,人来人往,每个人都有事做。现在,你该怎么办呢?”
来自中国台湾的科研团队,曾在普里皮亚季的隔离区采访了一位名叫Rosaliju的小学教师,她在核事故后曾短暂撤离到安置点,却因为无法适应新生活而回到家乡。
三十多年来,她独居在当年家人盖的房屋中,拒绝了乌克兰政府提供的福利,包括免费到切尔诺贝利的员工餐厅吃饭,以及住在有水有电的管制区内,每天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耕种、打水、砍柴、生火,守望者祖辈留下来的土地。
他们的回归并不合法,曾经多次被警方驱离,又重返,官方只好默许他们留下,但也不允许有更多人回归。
昔日繁华的普里皮亚季成为人烟稀少的“鬼城”,这座废弃的小镇已经成了记录苏联末期的博物馆,很多公寓还遗留着居民撤离时未能带走的生活用品。
狼、野猪和熊在周围茂密的森林中穿行,夺回了大自然的话语权。
很多人相信,在密林深处,也许存在“哥斯拉”般的怪物。但动植物在核辐射环境下的顽强生存有时超乎想象。
切尔诺贝利事故发生后,核电站附近的大片针叶林变成了鲜艳的橘黄色,随着高剂量辐射席卷该地,这片针叶林很快便死亡,沦为荒地。
但经过三十多年时间,这片树林几乎完全再生,白桦树等树木取代了以前的针叶林。不过,近年的一项无人机调查显示,这片树林的辐射仍高得惊人。
近年来,有一些勇敢的旅行者会前往切尔诺贝利探险,在相对安全的疏散区内,有数家公司在提供导游服务。
然而,核灾带来了很多看不见的伤害,并不是所有人都像普里皮亚季的回归者那样幸运。
事故中泄露的放射性同位素中,铯-137的半衰期为30.07年,锶-90的半衰期为28.9年,而它们都需要300年的时间才能衰变到目前强度的千分之一,届时这片土地才再次适于人类居住。
科学家们一直在检测切尔诺贝利及周围土壤、动植物体内的辐射量。
尽管空气中的放射物已经逐渐消失,但受到铯-137等放射物污染的土壤仍会威胁人体的健康,一部分放射物被植物吸收,随着牲畜吃草转移到其体内。危险的铯-137被摄入人体后,会损害人体细胞,甚至导致甲状腺癌等重大疾病。
除了导致细胞死亡、癌变等,核辐射对人类的精神状况也会产生影响。
常年研究辐射对健康影响的乌克兰国家医学科学院教授康斯坦丁·卡嘉诺夫斯基说,“近年来,已经得到证明,神经细胞分裂很容易受到辐射……这会导致许多疾病如认知障碍,行为障碍,思维障碍和情绪障碍,其中包括抑郁症和自杀。”
由于各方统计数据不同,对于此次核事故造成的伤亡人数至今没有定论。
据2005年联合国、国际原子能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和乌克兰政府等机构的联合报告显示,该事件死亡人数约为9000人,数百万人受到核辐射侵害,一直到今天,影响也未曾终结。
此外,切尔诺贝利周边地区的甲状腺癌、胃癌等发生率比其他地区高3倍,儿童夭折率比其他地区高5倍。
自切尔诺贝利事件后,核的恐惧弥漫全球各地,而今,这种恐惧已然归来。
2021年,切尔诺贝利核事故35周年之际,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在演讲中说:“灾难无国界,但我们能够携起手来,努力预防和遏制灾难,为所有需要帮助者提供支持,并实现强有力的复苏。”
但愿如此。